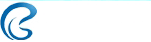王宠惠(1881——1958年)
王宠惠(1881——1958年),字亮畴,广东东莞人,光绪七年十月初十(1881年12月1日)出生于香港。
光绪十三年(1887年),王宠惠入香港圣保罗学校修习英文课程,在课余时间其父聘请当地的儒学名家周松石讲授国学典籍。光绪十七年(1891年),王宠惠入香港皇仁书院继续攻读英文课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王宠惠考取天津中西学堂(后改为“北洋大学”)头等学堂(即大学本科)法律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王宠惠作为北洋大学第一届学生毕业。王宠惠以优异的成绩位列第一届毕业生的第一名,他也是中国近代以西方模式培养的第一批法律家。
1901年,王宠惠游学日本。1902年,王宠惠赴美国留学,先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后转入耶鲁大学法学院,主修民事法律。190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JSD)。在美国学习期间,王宠惠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法学的训练,为了深入学习民法学,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还学习了德语。自耶鲁大学毕业后,王宠惠赴欧洲研修法学,被选为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在柏林比较法学会研修期间完成了《德国民法典》的英译,奠定了他在欧美比较法学界的地位。1908年,王宠惠在英国考取律师资格,其对英国法学习的成就亦得到承认。直到1911年9月间,王宠惠结束了在欧美国家9年的学习和研修,启程回国。
自幼年时起,王宠惠就结识了孙中山。后来,王宠惠赴国外留学,始终保持着与孙中山的联系,并尽可能地为革命事业工作。1904年,孙中山抵达纽约从事革命活动,正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学习的王宠惠经常赶到孙先生的寓所倾听革命思想,还协助孙中山起草了英文稿本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1905年、1910年,孙中山两次欧洲之行,皆约请王宠惠探讨宪法问题。后来,孙中山所完成的五权宪法理论,在宪法知识方面多借助于王宠惠。
1911年9月,王宠惠自欧洲回国,开始了他以法律之学报效国家的艰辛历程。王宠惠先后在南京临时政府、民国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执掌过外交、立法、司法、教育、行政等部门。但无论官居何位、职掌何事,王宠惠“为人谦和,手不释卷”的学人本色始终如一。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王宠惠曾出任法律编纂会会长(1917年)、两度出任修订法律馆总裁(1918年和1925年),主持多部重要法典的编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司法院院长、立法院顾问等身份参与议订多部重要法典。在编订刑法、民法和宪法过程中,王宠惠充分发挥了技术领导者的作用。特别是《中华民国民法》的优越性很大程度上源自《德国民法典》,其中王宠惠的技术性贡献自不待言。
1922年至1930年,王宠惠被推选为国际法庭候补法官,1930年至1936年任正式法官。但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际,当抗日战争爆发之际,王宠惠均以国事为重,离国际法官之任,而就国内司法之职。1927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各院组织成立,王宠惠任司法部长。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五院体制,成立司法院,王宠惠出任首任院长。1929年1月,他上任不久即在《中央周报》上发表《今后司法改良之方针》,明确指出司法独立为改革的主要方向。王宠惠对于民国司法改革之贡献体现在诸多方面,对民国法制影响最大则在于,该氏主张从功能上贯通立法与司法解释的体制隔阂,建立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法秩序。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元月3日,即任命年仅三十一岁王宠惠出任外交部长,在极为艰难的国际国内局势中,争取西方主要国家对革命政府的承认、办理保护侨民等对外交涉事务。从此王宠惠开始以法律技术领导的角色担负起危难之中的对外法律交涉。
1921年11月12日,民国北京政府特派施肇基(时任驻美公使)、顾维钧(时任驻英公使)、王宠惠(时任大理院院长)为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以争取国际同情、挽回国家权益。在华盛顿会议上,王宠惠先后提出“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案”、“废除二十一条案”、“废除势力范围案”。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提出“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列强借口该议题不在会议讨论范围之内而加以回避。华盛顿会议召开以后,王宠惠于1921年11月25日,向第六次全体委员会正式提出“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案”。 王宠惠所提之“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案”,虽未完全达到目的,终获得美国和英国在该问题上对中国的同情,并促成列强各国组成法权会议来华考察。
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集会开罗,商讨日本问题。由于开罗会议对战后中国利益,乃至远东格局关系重大,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该次会议。王宠惠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在拟定开罗宣言过程中,曾与英国方面发生激烈辩论,为维护中国权益及奠定远东格局发挥了关键作用。
王宠惠为民国政府的法制改革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在近代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功业。法律学者和政府法律技术领导者是王宠惠社会人格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整合就是学者法律官员。作为学者法律官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其社会绩效:
其一,从政府角度来考察其社会绩效。在“政府——法律家……民众”这一个社会圈子中,王宠惠需要直接对政府负责,完成政府指派的技术任务;就完成政府指派的法律任务方面,王宠惠已然尽心尽力,并卓有成效。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王宠惠为立法工作奔忙,在南京国民政府为司法改革筹划,他参与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民法》等均为当时最成功的立法,现今仍施行于中国台湾地区;该氏所倡议创建的大法官会议,现今仍然是中国台湾法律解释的中枢机关。在国际法律体系建构和法律交涉方面,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1912年至1945年,他始终在为国家的对外交涉提供法律技术服务:1912年办理对荷兰的保护侨民交涉;1918至1920年,修订各项法典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做准备;1921年参加华盛顿会议,交涉收回领事裁判权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为遏制日本侵略而展开争取国际联盟支持的对外交涉;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以抗战争取外援为外交重心……。1942年王宠惠主持“建构联合国集体安全讨论”,他逐步形成了国际集体安全的15点建议;至1944年在美国顿巴顿橡树园会议和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中国对联合国宪章的意见均出自王宠惠的15点建议,并有多项为联合国宪章所接受,从而确立了中国为联合国创立国之地位。在中国内外忧患接连不断的艰难境遇之中,政府对其法律技术领导的角色压力极大,使得王宠惠不能做出自己的选择,只能以政府指令安排法律技术任务,以法律技术任务安排学术研究的问题。然而,由于内外战争以及政府自身的问题,王宠惠在立法、司法方面的成就在当时未能充分彰显。
其二,从法律家群体的角度来考察其社会绩效。置身于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学者官员,王宠惠以挽救危亡、民族复兴为己任,于艰难苦困之危局中仍勉力为之,殚精竭虑于国家事务,他没有平和的条件把自己发展完善成为“知识创造者”和“圣哲”,难以立言传世。从他的个人著述来看,这些文字与其说是法律学术,不若说是应时的法律阐释。因为政府之法制建设之急迫需要,他往往需要广泛应付,不暇深究学理。例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急需一部刑法典,他即以《刑法第二次修正案》(1919年王宠惠出任北洋政府修订法律官总裁时主持修订完成)略加修改提交审议,1928年公布成为《中华民国刑法》。但在实施过程中,司法部门发现该刑法与中国社会之实际颇多悬隔,刑法学家亦以德国、意大利之最新刑法学说相驳难,最终导致该刑法施行不到两年即由刑法专家加以修订。王宠惠在法律家群体中为主流之代表,但在比较法研究的过程中,由于缺少中国固有法的知识背景和对中国社会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却不免以西学为体用。诚如蔡枢衡在《中国法律之批判》一书中对“主流”的批判:“三十年来的中国法和中国法的历史脱了节;和中国社会的现实也不适合。这是若干法学人士所最感烦闷的所在,也是中国法史学和法哲学上待决的悬案。”王宠惠的学术研究更多地成就了立法政策的法律学,却对法与历史、法与社会的层面缺少关照。
其三,从民众的角度来考察其绩效。学者官员之学术研究与实践最终需要对民众负责,通过立法确认民众权益,通过司法保障法定权益的兑现,通过对外交涉维护民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国民政府败逃台湾,民众的生活仍普遍艰难,民众的文化素质仍十分低下。例如据当时的抽样统计民国时期的识字率在20%左右,4亿多国民中文盲始终占绝大多数。就中国的教育状况,民国时期的教育家晏阳初曾说:“吾国男女人民号称四万万,估计起来,至少大多数一个大字不识,像这样有眼不会识字的瞎民,怎能算做一健全的国民而监督政府呢?怎会不受一般政客官僚野心家的摧残蹂躏呢?”这从一个侧面道出,在一个欠发达的国家里,纵然引入了西方学说体系,实现了法制现代化,但要真正实现法治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像王宠惠这样优秀的法律家其社会作用也是相对有限的。他所建构的法制体系,有很多是在中国台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了二十年以后,才显现出预期效果。
(有关王宠惠生平业绩的进一步内容,请详阅张生教授撰写的论文《王宠惠与中国法律近代化——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3期))